
Erykah Badu的房子被高大的树木和柔软的、凌乱的草堆包围着;它坐落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白石湖岸边,窗户装饰被涂成霓虹黄色,让人想起一些建筑师的眼镜框。外面的风铃在不规则的微风中嗡嗡作响。在里面,约翰·列侬的塑料小野乐队(Plastic Ono Band)的曲目从一系列看不见的扬声器中播放出来,声音覆盖了整个地方。
我们在她的客厅里面对面坐着,Badu告诉我,这些扬声器是她1997年搬到这里时买的第一件东西,同年她发行了首张专辑,Baduizm。在这中间的几年里,她成长为灵魂音乐最具远见卓识的人之一——不仅是歌手或词曲作者,而且是最广泛、最具创造性的制作人——她的房子里一片一片地充满了艺术和创造艺术的手段。
一些心爱的物品是朋友做的,一些是粉丝做的,还有一些是她的三个孩子做的,他们一有突发奇想就会画画。靠墙放着一把Wurlitzer吉他,一个极简主义的架子上挂着一把电贝斯,一对唱盘后面放着大量的唱片,两台唱盘之间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倾斜的架子上放着画架,还有两幅卡通画:一幅是八度,一幅是八度她的前夫安德鲁·本杰明她有一个儿子,也是她最大的孩子七岁。
现在是二月下旬,离她45岁生日还有两天,她计划举办庆祝音乐会。透过那扇长方形的大窗户,我们看到太阳平静地、闪闪发光地穿过湖面,还有远处达拉斯的天际线。这是八度出生和成长的城市,她的家族五代人都住在这里。我问她达拉斯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几乎笑了。“我只是喜欢这里的空气,”她说。“我喜欢鸟儿的叫声。”
她安静了一会儿,突然我听到了唧唧声,然后又是一声。八朵笑了——这不是她心爱的达拉斯鸟鸣声。它是一只宠物。
“我妈妈买了那只鸟作为马尔斯的生日礼物,”她说。“她的名字是,呃,斯巴克。”马尔斯是她最小的孩子,7岁。她的父亲是说唱歌手Jay Electronica。八度走到小笼子前,笼子不太干净。“她的生活条件很糟糕。”对小鸟说:“火花,我很抱歉。”对我来说:“我做到了不我要那只鸟。”她把火花带到我们身边,迎向阳光。这只鸟有一块跳跃的石头那么大,动作迅速、明亮、偏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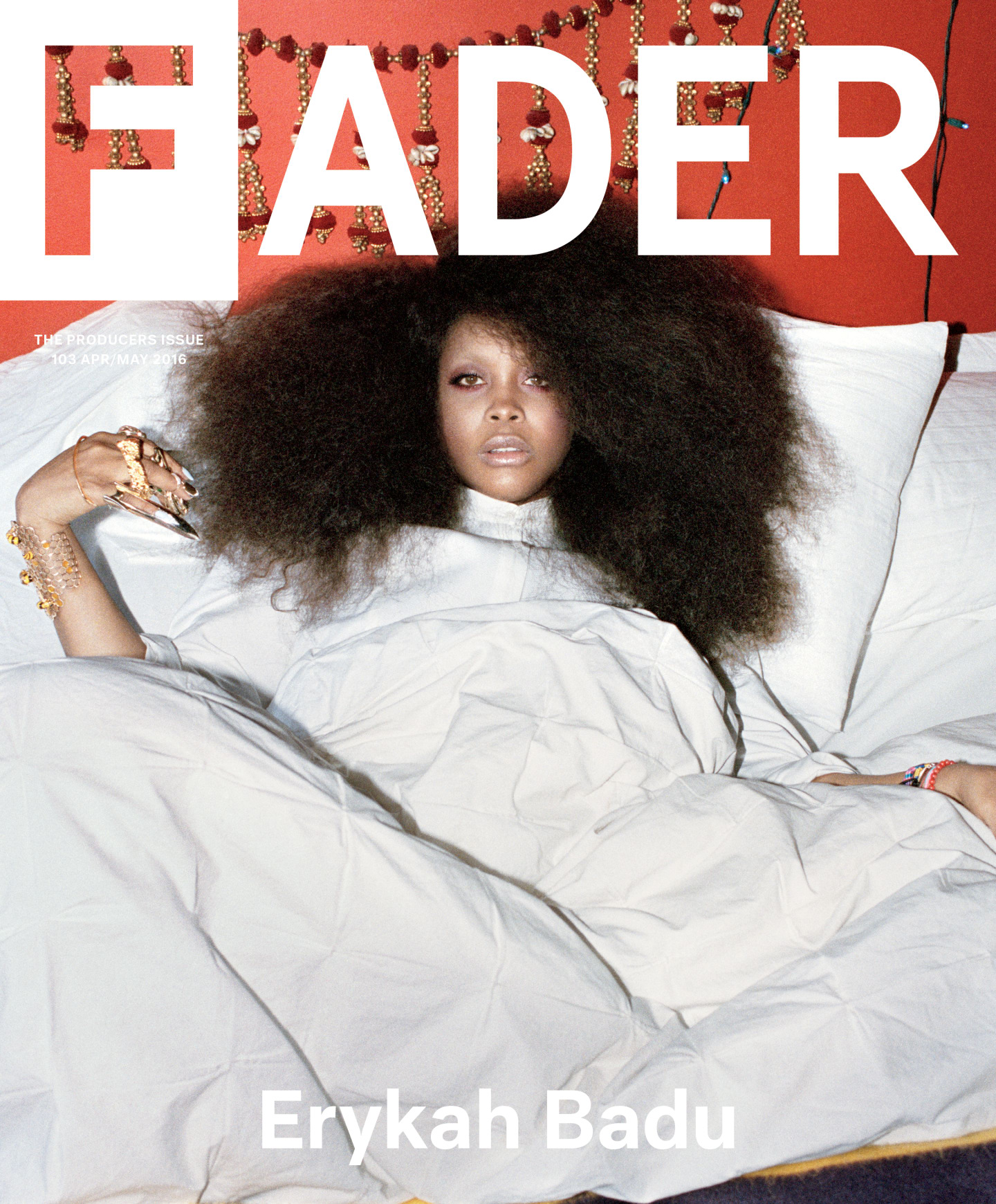
“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她说着回到达拉斯。“这是我创作的地方,我开始的地方,我……”她耸耸肩:这就是一切。她的家庭仍然是她生活中现实的基本单位。她的两位祖母都还健在,都快90岁了。一位曾经是她的会计,另一位是她的档案保管员,把多年来的文章、评论和专辑封面保存在一套整齐的活页夹里。尽管两人都已经退休,但巴杜笑着说,“在我的生活中,他们仍然非常固执己见。”她的母亲是她的保姆——“兼老板”。她的妹妹科利安(Koryan,又名科科)在屋子里溜来溜去,淡金色和紫色的辫子从背上飘过腰际;她是私人助理,酒店经理,背景歌手。她哥哥是卖商品的。她的表弟肯是她的房地产经理,和她一起旅行。
“无论如何都得付钱给他们,”Badu说。“不如让他们干活吧。”
她说话的声音非常清晰,非常灵活——即使在她安静的时候,或者为了喜剧效果而降低一个八度,整个房间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她说话时而拖腔,时而高亢。两根巨大的辫子从一顶针织帽里垂下,垂下她的躯干;她的脚趾被涂成与房子一样的亮黄色。
我开始问一个问题,中途意识到她正皱着眉头看着我,嘴角带着讥讽。“再说一遍?”她说。“我在看7号。”我还没来得及重复一遍:“孩子!我还以为是你爸爸来接你呢。”
“是啊,”一个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我们要去吃点东西什么的。”7 - 18岁,瘦骨嶙峋,一个大嘴巴的父亲在世界上走来走去,慢悠悠地走进客厅,拥抱他的母亲再见。
下午晚些时候,Badu将与Seven见面,andr
我问冰箱里有什么。
“我不知道,去掉顶部的辣酱?”你一开门就闻到辣酱的味道。我不会去那里,但那里……就是一堆打开的屎。”她露出明显的骄傲的微笑。“他工作很努力。他从3岁到7岁在家教育,所以他很专注。他就像个书呆子。”Seven喜欢艺术,设计衬衫和纽扣,从五年级开始学习拉丁语:“所以他知道怎么拼写一大堆狗屎。”她说,明年在大学里,“他将主修心理学,辅修商科,这样他就可以骗别人买他的东西了。”这是他的主意。”
Badu的第二个孩子Puma今年11岁。她的父亲是达拉斯本土说唱歌手D.O.C.。她唱歌——“她就像我一样,”Badu说——她在一所法语浸入式学校上学,在那里她开始接触普通话。一年级的玛尔斯也去了一所浸入式学校——她学的是西班牙语。
“我只是想确保,”Badu说,“无论何时我接管这个国家,我身边都有一位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一位和平大使。”

“做一个助产师,或者做一个妈妈,甚至是做食物——这只是呼吸和信任,让创造力流动。”
我们来到厨房,八度即兴布置了一些水果:新鲜切碎的菠萝放在中间,浆果在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波浪中向大方形盘子的边缘移动。她用四五勺又长又细的生菜做装饰;在每棵树的白色脊骨上,她均匀地放置了一排树莓。
展示的复杂性令人印象深刻,我是这么说的。
“谢谢你,”她说。“这是艺术。对我来说一切都是艺术。我们在创造艺术”——这指的是我们正在进行的采访。“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连厨房也像是一幅大型拼贴画:每平方英寸都贴满了她的孩子、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亚辛·贝伊(Yasiin Bey)和已故制片人J·迪拉(J Dilla)等著名朋友的绘画和照片。
“这是一份高碱性的午餐,”Badu说。“我们会有很多能量。”
我们把水果搬到房子后面的餐桌上,八都把一块多余的生菜叶子喂给了玛斯的另一个不太可能的、半想要的宠物:一只名叫小汤娅的豚鼠。附近的窗台上放着七个刷过漆的纸板箱。八朵告诉我,她正在开始写自传的过程,这些盒子是一种大纲。“我只是画了它们,”她说。“我要把它们排在桌子上,每一章一个,我要把东西放在每个盒子里,这样我就能看到我在做什么了。”红色代表家庭,橙色代表性——“婴儿爸爸,爱情”——黄色代表创造性生活,绿色代表她作为助产师和“整体治疗师”的工作,浅蓝色代表音乐,深蓝色代表灵性,还有一个紫色的盒子,她说这是一个谜。
每隔几分钟就会有电话打来。前段时间,八朵把她的手机掉进了一碗汤里,所以她不得不用扬声器把每一个都录下来。
打电话的人都有点小心翼翼,每个人都陷入了一些关于她生日聚会的奇怪细节,这些细节不能在电话里解释清楚。“他们每年都喜欢给我一些惊喜,”她在电话间隙说。“我喜欢破坏它。”
唯一诚实的人是八度的祖母甘妮。他们的交流充满了爱,都是咕咕叫,最后,奶奶兴奋地尖叫着为孙女过生日。
“我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女人,”Badu说。
“我知道,”甘尼说。“你是我的宝贝。”

现在是德克萨斯州“超级星期二”初选的前一周,所以我问了一些政治问题——当然,我的意思是问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他威胁要筑起的各种墙,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态度上的。
“哦,我不相信那些狗屁东西,”她说。
“墙上?”
“政治。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发言权,这是一个节目,这是一个游戏。在较小的范围内,我认为你的城市代表和地区代表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非常认真,然后当他们站得更高一点时,这就变成了一场表演。每个人都很兴奋。”
“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疯狂的事,”她谈到特朗普迄今为止的成功时说。“这是真的吗?”但是”——若隐若现地耸了耸肩——“如果计划是这样的话,它将成为现实。”
Badu提到了2008年的专辑新美国第一部分(第四次世界大战)这证明了她自己的能力,通过艺术,她不仅能谈论社会问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能预见社会问题。以她的歌曲《Twinkle》为例:他们让我们不受教育/生病和沮丧/医生我现在上瘾了/我被捕了。
“我感觉它来了,”她说,警察暴力危机引发并维持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我真的很想把我周围发生的事情写下来。我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写进了那张专辑。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现在写,因为我已经写出来了。”
她把我们的政治现状看作是对不止一个方面的严肃程度的考验。“当警察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像个混蛋一样组织起来,”她说。“但我们能组织起来阻止黑人对黑人的犯罪,或者穷人对穷人的犯罪吗?”因为,你知道,穷人是新的黑人。你现在不必非得是黑人了。”
像这样的立场,其中一些令人惊讶的保守,已经成为Badu形象中越来越突出的方面,尤其是在网上,在我访问达拉斯几周后,她呼吁女生校服应该穿更长的裙子,在Twitter上引发了一场风暴。她使用当今的病毒式传播工具来传播和捍卫不受欢迎的立场,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适合她:对Badu来说,艺术始于个人的声音,无论多么非正统。

“我觉得碧昂斯的做法很酷,”她说。肯德里克·拉马尔有意识地通过展示他所在社区发生的事情的另一面来书写和影响改变。信不信由你,NWA一开始也是这么做的。‘Gangsta, Gangsta’实际上是一种恶搞。”在谈到自己的观点时,她毫不费力地唱出了这首歌的第一节:
这里有一些关于像我这样的黑人的事
就不该被放出来
冰立方,想说
说我是个疯婆娘
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抽大麻
现在我就是你读到的那个混蛋
夺走一两个生命,这就是我所做的
你不喜欢我的生活方式,去你妈的
这是个帮派,我是其中一员。
这是Cube的一种表达方式:这就是你创造的东西。他不是黑帮。但我觉得他们感觉很好。我想只要能让你最爽就行。激进分子的女人还是黑帮的女人?黑社会的女人更多一些。”
所有这些——对政治活动的性质和效力的玩世不恭,对幽默作为抗议手段的兴趣,如果不是改变的话,以及关于性作为斗争的反动机的随口台词——证实了我一直对艾瑞卡·巴杜的怀疑。作为一名歌手、词曲作者和表演者,她在灵魂音乐史上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一贯的讽刺。自蓝调的鼎盛时期以来,没有人比她更有趣,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比她更能意识到她的幽默是如何扭曲了她周围的世界和创造她的历史的。她动作急促,嗓音粗犷多变,与其说她是比莉·霍乐迪(Billie Holiday)和戴安娜·罗斯(Diana Ross)的后代,不如说她是对这些前辈的评论,以及对赋予她们力量的风格和习惯的评论。
这一点在观看八度的现场表演时表现得最为明显,顺便说一句,八度认为这是她最基本的天赋:“表演就是我所做的,”她告诉我。在舞台上,她风趣幽默,在数字之间讲述故事,常常设定一个令人信服的前提,以至于随后的整首歌都像是一个细长的、有米长的笑点。她用一种缓慢而夸张的旋转——不是舞蹈演员的动作,而是舞蹈演员不可思议的模仿——或者用一种夸张的向上的姿势,朝向灯光,削弱了她最深刻的感受。她的表演充分意识到表演的技巧和愚蠢。她比几乎所有人都更善于利用实际存在带来的机会,发挥自发的创造性控制,用熟悉的材料塑造出真正新的东西。
她说,这种感知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蓝调背后的荒谬,蓝调是达拉斯伟大的文化遗产之一。“那是我的根,”她说。“我们在达拉斯有一个叫做深Ellum的地方。深埃勒姆是镇上深沉、浓郁的蓝调区。”她把那些成群结队来这里演奏的传奇人物——她的前辈们一一列了出来:Muddy Waters、B.B. King、Johnny Taylor、Denise LaSalle。
“这是一门即将消亡的艺术,”她说,但一点也不伤感。“这很好。事情就是这样,要么进化,要么死亡。”


八朵在她长大的房子里,完全自然地生下了她的三个孩子;现在,她是一名完全有资格的助产师,正在努力获得助产士的认证。“我爱做母亲,”她说。“这对我来说很自然。做一个助产师,或者做一个妈妈,甚至是做食物——这只是呼吸和信任,让创造力流动。”
她的助产师生涯始于2001年,当时她向她的朋友阿菲亚·伊博姆(Afya ibomu)——嘻哈乐队Dead pres成员斯蒂克的妻子——发誓,她将帮助她生孩子。在经历了54个小时的阵痛和疯狂的国际航班回到纽约后,Badu在那里接住了孩子。从那以后,她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在巡回演出和录音之间,她被课本、论文、研究、解剖学课程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助产士所困扰。
八度开着一辆光滑的黑色保时捷来到分娩中心,车身很低,车牌上写着“她病了”。在里面,她的助产士导师,一个留着一头短发的白人妇女,正带领大家参观宽敞、灯光温暖的主产房。
“她的肚子很大,”助产士说。她也是该中心的老板,她正在为一小群人设定一个场景:“宫缩每五到七分钟一次,而且越来越强烈。”
她继续角色扮演,从阵痛到快乐分娩:孕妇穿过中心的门,呻吟越来越强烈,到处都是倚靠——靠在床上、马桶上、墙上。每走一步,助产士都会给出一个可能的选择。你可能会在浴缸里生孩子,或者在床上生孩子,或者站在淋浴间里生孩子。她的声音,即使在表示痛苦时,也流露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听她说话,周围是10到15对全神贯注、惊恐不安的未来父母,你可能会想象——或者,如果你曾经目睹过一个孩子的出生,你可能会记得——这段经历中更可怕的方面:浓重的铜腥味,孩子从身体里滑出来,像鱼一样,进入昏暗但无可反驳的光线中。显然,这位助产士——如此镇定自若,如此庄严自在,如此熟悉与死亡的接近——在她的听众中激起了一种警惕的敬畏。除了她,唯一一个微笑着、移动自如、踮着脚尖跳来跳去的人就是八度。

参观结束后,我们回到她家。天黑了,市中心的灯光像静电一样掠过湖面。八度的妹妹科科找了一个不充分的理由要离开。“我得……”她说,“嗯,去教堂。”
“啊,”八度说,想着她明天的生日。“你得为我做点什么!”你不能在周四晚上去教堂。你们的行为都很滑稽。”
科科走后,Badu走到她的唱机旁,快速地做了一组DJ: Biz Markie的《Vapors》、Beanie Sigel的《Roc the Mic》、Musiq Soulchild的《Just Friends》、Jay Z的《Hustler》、Carl Thomas的《I Wish》、Quest部落的《Check the Rhime》。“我喜欢摇滚派对,”她微笑着说。
等她吃完,我们就去厨房吃米饭、仿鸡和八都院子里的青菜。玛尔斯跑来跑去,从盘子里拿起食物,然后不知怎么地哄骗她的母亲同意帮她数她所有的Shopkins玩具,那是一大堆我从未听说过的坚硬的塑料小雕像。当小女孩整理她的盒子时——“她有洁癖,”她妈妈告诉我——八度向她解释了围绕玩具而产生的校园经济。
“比如说,我有两支布洛安尼斯,而有人可能有一支莫利·莫卡辛要交易。”
“我已经有了莫莉·莫卡辛,”马尔斯说。
“嗯,我知道。我只是举个例子。被假设。你能这么说吗,假设一下?”
“假设”。我无法表达这个孩子第一次就做得如此完美是多么满意。
它的意思是,就像一个虚构的事实。一个演示版本。”
于是他们数着数着,把每一幅微型画举到我面前,让我看到它们,用它们不太可能的名字来称呼它们:Dressica, flusous, Penelope Treats, Peter Plant,等等。总共有123件东西——收集它们显然既是母亲的工作,也是孩子的工作。马尔斯有时会哼唱蕾哈娜的《Work》,八度也跟着哼唱。“我喜欢那首歌,”Badu说。

“要么进化,要么死亡。”
Erykah Badu生日那天的下午,我走到夜总会,去见Badu乐队The Cannabinoids的乐手们,派对将在当晚晚些时候举行。他们都是些有趣的三四十岁的小伙子,穿着运动衫和时髦的运动鞋,吃着饭,调整着设备,期待着八都的到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做一个试音。你可以看出,他们已经习惯了把时间作为一种可协商的东西:没有人有一个明确的开始时间,他们只是出现了。
Big Mike, Badu粗暴但友好的巡演经理,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跟着她。他解释了专业精神是如何在八度世界发挥作用的:“她的态度是,‘我到这里时不要看。到时候把我的东西准备好就行。做你们该做的就好。’”他告诉我,有时乐队是最后一刻才来的,有时是偶然的。“但他们总是希望我们回来。我们得到的工作比我们能做的要多。”
船员之间的气氛几乎是亲切的;他们都在开玩笑,你会想到一个一起环游世界好几次的团队会用那种“叽叽喳喳”的简写。有人回忆起曾经因为错过了从波兰回家的航班而爆发的一场争吵,这场争吵是由八度结束的,他把一个杯子扔到房间的另一边,告诉每个人都忘了这件事。另一个人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们都挤在伦敦的一个小俱乐部里,也许是吧,坐在那里,听着巴杜用手鼓伴奏的慢节奏歌曲《Bag Lady》的糟糕表演,演唱者不知道这首歌的创作者就在舞台下面等着,一边拍着头。
还有一群更年轻的人在附近徘徊:Badu的开场演员,包括奥布里·戴维斯(Aubrey Davis),一个21岁的瘦高人,戴着眼镜,扎着浓密的马尾辫。Badu通过Seven找到了戴维斯,戴维斯是一名说唱歌手,与德雷克的声音相似,名为ItsRoutine,她已任命戴维斯为她的独立唱片公司Control FreaQ的艺人与开发部主管。Control FreaQ的核心承诺是,在商定的10到15年期限后,归还其艺人音乐的所有权,这就是戴维斯现在签署的协议。
他看起来有点焦虑,期待着他的短集,他描述了帮助写八度翻拍的《电话先生》的过程,一首新版本的曲调让人头晕目眩Badu最近的混音带,但你不能用我的电话。“她从未见过我在电脑上使用的程序,”他说。“但她给我看了很多我都不知道的东西。如何安排人声,等等。她基本上是自己掌握了这首歌。”
制作《Phone》的过程表明,八度不仅是一个创造性知识的宝库,而且是一个自愿的学生,乐于指导和学习新人才。她说:“现在孩子们的写作方式不同了。”“鼓是不同的,所有的东西都被困住了。我觉得,‘哦,我能做到。’”
她在录音的制作人扎克·沃特(Zach Witness)发行了《袋女士》(Bag Lady)的混音版后遇到了他,他也是21岁。首先,两人创作了《Cel U Lar Device》,这是《Hotline Bling》的混音版,是给喜欢德雷克这首歌的大麦克的生日惊喜。然后,在SoundCloud上获得了压倒性的好评后,Badu打电话给Witness,请他和她一起制作一整manbext万博套与手机相关的翻拍。两人在他简朴的录音室里以每天一首歌的节奏工作,录音室位于达拉斯的一幢平房里,他就是在那里长大的。最终,他们创作出了一系列作品,证明了Badu有能力将自己标志性的歌曲风格与现代的声音和提议结合起来对我们依赖技术的现状进行了有趣的分析。
很快,我听到八度在舞台上唱着歌,要求调整灯光和麦克风的音量。后台空了,大麻乐队走向他们的乐器。大麦克没有撒谎:八度站在一个粉色的、病态精细的大脑复制品旁边,她对乐队的领导是轻快而准确的。她想要达到精确,她想要快速完成。
 乌拉尼娅·特雷尔的连体裤
乌拉尼娅·特雷尔的连体裤
试音结束后,我和八都开车回她家。在她自己的聚会之前,她必须帮助彪马为学校舞会做准备。在路上,她问我想不想听她为今年挑选的生日歌。我说当然,她把视频放到YouTube上,对于一个手在方向盘上的人来说,这是相当快的。那是妮娜·西蒙娜(Nina Simone),她穿着一件飘逸的长裙,一串珍珠项链在脖子上摇曳。
做我的丈夫,我就做你的妻子
做我的丈夫,我就做你的妻子
做我的丈夫,我就做你的妻子
爱你们所有人,直到你的余生
八都跟着西蒙娜的肩膀向内弯着。他们的声音像这样在一起听起来很好;每一个都是不同的,但随着歌曲的深入,它们达到了一种融合。
“这是一首很棒的生日歌,”唱完后我说,Badu说,“是啊。”
当我们到家时,彪马娃娃面带粉红花边,脚穿黑色靴子,和一个朋友站在那里准备出发。八朵对她的衣服,她长长的、卷曲的头发,以及她是否应该穿丝袜去跳舞都很挑剔。很快,彪马准备好了,她的父亲来接她。Badu坐在那里摆弄着她的手机,确保她把所有的朋友和家人都列在了她聚会的名单上。
当卡尔·琼斯出现在房子里时,天已经黑了。琼斯曾担任制片人偏僻地区的并创建了黑色炸药在那里,当八朵来做配音工作时,他遇到了她。现在他们是一对拥有自己制作公司的夫妻;他们的第一个项目是八度作为灵魂列车奖的主持人而备受赞誉。“她有一个很棒的观点,”琼斯告诉我badu是一个喜剧演员。“她就像现代版的卡罗尔·伯内特。她扮演了很多角色,而且她是一个非常机智的作家。”
八朵溜出去换衣服去参加演出,当她出现的时候,她穿着一身黑,戴着一顶高高的宽边帽。”不到的她像唱歌一样对琼斯喊道,“你能帮我穿鞋吗?”两人之间有一种温柔,一种快乐的沉默,他冲过去,抓住她的手臂保持平衡,而她则把脚塞进战斗靴。
即使在演出的晚上,八度也会自己开车去上班。她戴上一副时髦的眼镜,给保时捷加油,琼斯坐在副驾驶,一如既往地开着车:既担心又高兴地快速行驶,尤其是在匝道上,不耐烦地绕过限速的司机。她绕着会场转了一圈,看看排队的人,然后把车开进了后面的停车场。
后门滑了出来,就像车库一样,Badu把车开到了后台,在那里,是的,乐队,是的,戴夫·查普尔——当晚的主持人,是的,几个灯光和音响技术人员,是的,家庭成员,但似乎还有数百名热情的、色彩鲜艳的、可疑的随从在周围转来转去。当八度从车里出来时,每个人都蜂拥而至。她很亲切:握手,拥抱,拍照,拥抱Chappelle,拍更多的照片——所有这些都在她看到她的试衣间的第一英寸之前。
在一个装饰着鲜花和复杂植物的空间里,她燃烧了一大束鼠尾草,然后安静地旋转着。当净化仪式完成后,她看起来很开心。她扫视了一下房间里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过一个如此……花香的生日。这么多礼物。”演出开始了,她冲到舞台前,突然听到奇科·德巴格的声音。
“奇科?她说。他是摩城唱片家族成员德巴格的弟弟。“哦,大便。我一定要听听。”

很快就轮到她表演了。我站在旁边,看着八度做着她在过去几天里经常告诉我的她喜欢做的事情。所有的旋转和旁白,向她家乡的人们表达爱意。她坚持说,这些光线总是带着蓝色,像手指一样细细的一缕缕伸向她。她喜欢把注意力集中在她的乐队上,经常要求每个成员都献上独唱,有时候,当她提到应该在她身后唱歌的科科(Koko)时,却找不到她的妹妹。
演出结束时,八度唱着《颤栗的朋友》,她最近发布了对坎耶·维斯特的《Real Friends》的改编,美好的事情开始发生。
朋友八度唱着。一个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词/但大多数时候我们用错了它…
在科科的带领下,她真正的朋友们涌上舞台,给她一块蛋糕和一顶薄薄的金冠,可以盖在她的帽子上。安德烈在台上——当他溜上舞台时没有人注意到他——当Badu看到他并把他介绍给4000多名观众时,屋顶几乎要飞离大楼。
很快,Chappelle拿到了麦克风,不知什么原因,他开始讲述一个关于开车去肯塔基赛马场的故事,当时车里坐着Erykah Badu,收音机里放着Mtume的《Juicy Fruit》。“我忘了我的朋友是世界上最好的歌手之一,”查普尔说。“突然间,她开始动手了,整辆车都在敲门。”
随着他的继续,乐队开始即兴演唱这首歌。
“这个女人太特别了,”他说,这是戴夫·查普尔说过的最真诚的话。
“所以让我们为我的朋友鼓掌吧:Erykah!”
订购Erykah Badu的《The FADER》,在2016年5月10日上市之前。
发型乌拉妮娅·特雷尔,化妆特蕾西·摩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