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nt Reznor谈论过去、现在和未来
来自杂志:发行88,2013年10月/ 11月
就在“九寸钉”在今年的Lollapalooza音乐节上撕下头条的几天后,特伦特·雷兹诺(Trent Reznor)离一个更艰巨的手术的最后阶段只有几个小时了——一个根管手术。但这位48岁的老人精神状态很好,正在比弗利山庄的马球酒廊(the Polo Lounge)喝咖啡,尽管这个地方似乎更适合细条纹西装,而不是NIN经典美学的皮革和链子。雷兹诺穿着t恤和牛仔裤,不显眼,他的举止与他时尚感中的成熟冷静相呼应。
他既放松又警觉,健谈但又积极矜持,措辞谨慎,不时发出警告,比如“我觉得谈论这个话题有点无聊”、“我马上就闭嘴”、“我是以一个老家伙的身份说这些话的。”然而,这次谈话证明了他对过去和现在以及接下来的事情同样精通。
当你创办NIN时,你对未来有多清醒?给大家一点背景,80年代早期合成器流行音乐的大爆发是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得到了我的第一个合成人,我一直对加入摇滚乐队的想法很感兴趣。我知道我想这样做,但为键盘手找一个角色总是很笨拙。好的例子并不多。我不想在艾默生,莱克,帕尔默这类破公司工作。所以看到这种新技术——鼓机、测序仪——我感到非常兴奋。随着80年代的发展,吸引我的是电子产品的更积极使用和芝加哥的Wax Trax标签,它也吸收了一些发生在欧洲的东西。它给人的感觉是摇滚乐的激进力量,但它打破了齐柏林飞艇创造的那种必须有吉他,贝斯,鼓,必须以蓝调为基础,必须是这个,那个和其他该死的东西。我一直喜欢避免怀旧的想法。我理解它的目的,(有时)我可能会为此感到内疚,因为很难完全避免,但我喜欢尝试推进新事物的想法。
你还记得你第一个合成人的型号吗?是的。我不是在一个高收入的家庭长大的——我的祖父母把我养大——我得到的第一个合成人是穆格公司生产的一个叫做Prodigy的廉价合成人。当时大概是7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但只要我能拿到其中一件东西,就已经让我兴奋不已了。不久之后,第一个MIDI定音仪问世了,这是一个插在Commodore 64上的墨盒,它允许你通过计算机简单地排列零件,这在当时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我敢肯定,今天的大多数音乐家看到这种设置会发现它非常有限。我的声音制作工具库里有一架父亲送我的沃丽泽钢琴。它本身就是一件很酷的乐器,加上几个效果踏板,我可以让它失真。如果你以正确的方式演奏 ,它听起来像范海伦的轨道。所以突然有一个真正的合成器在当时似乎是无限的。
当我看到今天在笔记本电脑上,甚至在GarageBand或iPad上,声音设计和作曲工具的范围——今天的孩子们被宠坏了!你可以用那东西做无数的事。但那时候,你不会认为我一次只能发出一个声音。当你投资那件装备时,你——或者至少是我——花了数年时间学习你能用它学到的每一个技巧,并充分探索它。今天,这有点像音乐消费:你可以接触到很多东西,我认为人们很少像过去那样花那么多时间来从中得到他们能得到的东西。
“我一直喜欢避免怀旧的想法。”

你在自己的工作中有没有看到这种加快的节奏?这几年你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了.在我看来,有两个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我工作得更快,我就不那么和自己较劲了。部分原因是保持清醒。其中一部分是要足够成熟,明白我所做的工作可能很糟糕,如果是的话,我可以把它扔掉。尽管这句话很简单,但当我看着一张白纸,心想:“这一定是最好的歌——我是怎么写出这么好的歌的?”我被那种疯狂控制着。
但作为一个做音乐的人,作为一个创作者,我确实发现(消费的速度)令人不安。嗯,我对此百感交集。当ipod问世时,我抵制了它们,因为我喜欢去Tower唱片公司。这种体验和走进去看东西的仪式,发现一些我在其他地方不会有的东西。我也喜欢在克利夫兰的Record Revolution这样做。我手头的现金非常有限,但每一分钱都花在了那个很酷的新4AD导入上,我没听说过,但封面看起来很酷,标签也很酷。带着一些东西回家,把它从塑料里拿出来,闻起来有一种特定的味道,阅读里面的音符,戴着耳机听——这种消费仪式强调的是音乐。这是一个优先事项;那不是你在背景里放的东西。你是来听音乐的。 Phone off the hook, don’t fuck with me, I’m listening to this stuff. If you invested in an album, then you played the shit out of it. Even if you didn’t like it, you kept listening to it because it was one of a limited number you had access to. That definitely changed my tastes. If The Clash’s桑地诺的支持者今天才出来,我就不会花时间去解读里面发生了什么。如果Talking Heads保持在光明中今天出来了,我听起来会觉得,这太他妈奇怪了,我不明白,管他呢,接下来呢?但因为我强迫自己突破了那个障碍,它就变成了一种思维扩展的东西。我不能告诉你最后一次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在某件事上。只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想有一个黑胶唱片收藏,但我没有把我的东西放在一起,而且我经常搬家,现在还有孩子和其他事情在碍事。但我喜欢这样,我是听着这样长大的。
不管怎样,在我拒绝之后,我想我们在巡演,我意识到我实际上听了更多的音乐,因为我有数百张专辑,而不是我拖着到处走的cd。我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单独听音乐,但我会花更多时间听大量的音乐。 这是好还是坏?
似乎人们在浏览电子邮件、发推特或其他上网时做的事情时就会消费音乐。这对我的音乐创作有影响吗?不是有意识的。我仍然在努力创作需要听很多次才能理解的音乐,并且在听了50次之后就能揭示出一些东西。我认为会有很多人(给予这种关注)吗?我没有看到明确的证据,但我希望如此。
几年前,你开始大量使用社交媒体,然后收回了,是的。(笑。当[NIN]脱离Interscope后,我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投身其中。我需要弄清楚人们是如何消费音乐的。不是我,但一个16岁的孩子是怎么做到的?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这个问题,那时推特刚刚起步。
起初,我觉得它很有趣。我一直在想要解构我为自己创造的神话,我想人们意识到我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也许我有幽默感,也许我在白天是清醒的。我喜欢迷惑别人或让他们困惑,但我也意识到这有点粗俗。也许这只是我现在老了,但我们所陷入的文化,真人秀和社交过度分享,总的来说,这只是一种庸俗的心态。这是它的一方面——作为一个人,我能感觉到,我不想太深。
另一方面,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音乐有一种神秘感,我认为音乐需要保持这种神秘感。再一次,这一切都回到了是什么造就了我。当我长大的时候,我不知道平克·弗洛伊德长什么样。我当然没有看到他们的现场,我也没有被视频轰炸,因为没有MTV。我不知道他们的沙拉长什么样。或者他们是否有沙拉。因为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我被允许解读音乐[和想象]我想要它是什么样子。这有点像看书和看电影。当我在想象中填写时,这个集合看起来更好。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就不点名了,我对现在的乐队的音乐很感兴趣,我偶然发现了一个推特账户,上面写着,哦,这家伙有点混蛋。仅仅是他所谈论的东西就足以让我厌烦,以至于我听的时候音乐听起来都不一样了。我知道这不公平,但是 我想让我的个性远离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东西, 就是音乐。
“我仍然在努力创作需要听很多次才能理解的音乐,并且在听50次之后就能揭示出一些东西。”
这张新专辑似乎是你自《Pretty Hate Machine》以来最接近于制作纯舞曲的专辑。你的灵感是什么?这不是计划。通常,在我开始录制新唱片或收集新东西之前,首先会花大量的时间在黑暗中摸索,看看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感到鼓舞。以The Slip为例,启发我们的是这种规则,我们说,让它听起来像车库电子产品。没有什么是固定的,没有多看一眼,没有人声的调音。所有东西都戴上麦克风,不要直接戴。在开始唱新歌之前,我们会检查这些规则。一切都做得很快, 这很有趣。
对于这张唱片,我倾向于在一台mpc类型的作曲家上写所有东西,这台Native Instruments机器是我在办公室里安装的。我玩得太开心了,这成了我自己强加的限制。我不会使用 键盘;我不会用吉他,因为它们很无聊。我要用卫生巾。我就这样开始吧。在那个阶段可能产生了上百个不同的想法。然后我会把它们带到楼下真正的工作室,和我的同事阿提克斯·罗斯(Atticus Ross)和艾伦·穆尔德(Alan Moulder)一起对它们进行润色。
也许这是对我(为电影配乐的工作)的一种反应,我的工作都是关于质感和对不同情绪、氛围和气氛的研究。节奏对我来说更有趣。我并不是在听大量的电子音乐——反正不是有意识的。我不是想做一张人们可以跳舞的唱片。
流行音乐和都市音乐似乎都在你早期的模式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你感谢《王子》和《全民公敌》漂亮的仇恨机器衬垫。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脱离这些影响的?我在新奥尔良的那段时间脆弱的我把外面世界发生的一切都关在一边。我更喜欢老伊基·波普和鲍伊,而不是当时发生的说唱摇滚之类的东西。我现在听很多当代的东西,只是想看看发生了什么。
在这张新唱片中,我没有像过去那样审查自己。我有时允许自己像罂粟花一样。例如,“come Back Haunted”一开始就有一种节奏和跑调的低音。在最后的安排中,我想到了一些声音漂亮的仇恨机器-那些我还在用的合成人。这是在逃避吗?你知道吗,照做就是了。我这样做了,我知道它会把人们带回来。我听过很多人说,“听起来更像是。漂亮的仇恨机器比你做的任何事都重要。”是啊,因为是同一个合成人。我承认这一点。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绝望,嘿,还记得这张有500年历史的专辑吗?我觉得这么做是对的。
回到那些碎片里一定很酷吧漂亮的仇恨机器模板与今天的技术在您的处置。几年前我们重新录制了那张专辑,因为不管是谁买了版权,他妈都想为所欲为。实际上我们试着重新混音,但那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你想做一些比1988年那种大洞穴混响更有品位的东西吗?这有点亵渎神明。这些东西创造了情绪,当情绪发生变化时,它就变成了一张不同的专辑。所以我们最终只是重新制作了它。但我们确实花时间听了这些东西,这让我恢复了精神。你知道,这就像重温你很久以前的论文一样。你记得写它的人,通过这个棱镜看你自己是很有趣的。
你提到过你更关注当代的东西。你最近都在听什么?我已经谈到了我们应该从那些很酷的独立游戏人群那里听到的东西。有些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很多都是扯淡。我认为A$AP Rocky的制作非常出色。我喜欢《揭秘》的初次亮相——它非常明显,也很棒。有些东西让人觉得很诚实而且听起来很有趣。我一直都很喜欢灰熊。嗯,给我看一件事,我会给你一个赞成或反对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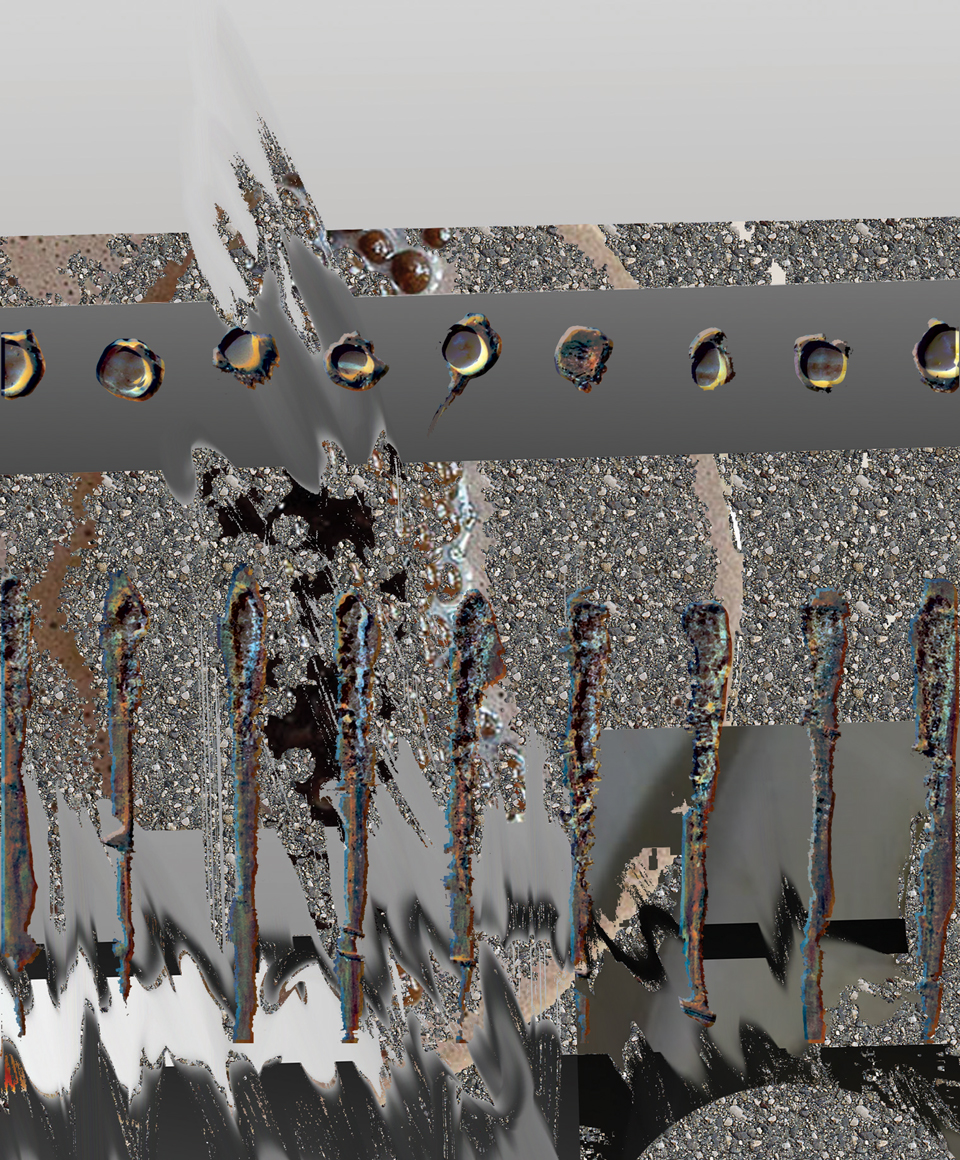
你在想什么Yeezus吗?哦!我觉得那张唱片很不错。在音乐上,我很喜欢它。我了解坎耶一点点。这些年来,我们在节目中打过招呼,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迷人的角色,能够用非常棒的音乐来支持一些荒谬的事情。不可否认。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意识到他的时候,是那些Jay Z的歌曲和加速样本。我讨厌那个,我只是觉得那太烂了。然后我听了他的独唱,好吧,我懂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断提高标准。 Even when he fails, it’s usually not for lack of trying. I appreciate that. And although I don’t agree lyrically with what he’s going after, when you add up what it is to be an entertainer in the year 2013, he’s on the cutting edge of that paradigm—that kind of vulgar oversharing.
你怎么看现代嘻哈开始模仿你们几年前的审美选择?嗯,我被它吸引是因为我觉得它听起来很有趣。我喜欢它不是因为它听起来像以前的东西,我喜欢它是因为它不让人感觉懒惰。
似乎有些人在EDM世界已经拿起了你的工作咄咄逼人的线索。你的立场是什么?我喜欢电子音乐的声音。我一直都是。当我们在91年的第一届Lollapalooza音乐节上突然出现时,我希望人们不要注意到我们在舞台上有一个磁带架。对于使用排序器、回放或合成器,人们的心态也大不相同。我们会把米力香草化。看到它变成一种主流(音乐)形式是令人兴奋的。《如何摧毁天使》在科切拉演出,在我们继续之前,我们走到舞蹈帐篷,它比我们演出的帐篷大10倍。我走进去,看到一群人比我以前演奏过的任何乐队都要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完全可以和任何其他美国dubstep贝斯废话互换,一群人完全疯了。舞台跳水,混乱,灯光,成千上万的激光等等。
不可否认,这很有趣。我得到了能量。如果我在那个年龄段,我会被它吸引的。但我并没有从实际的演唱技巧和每一场表演的创新中得到太多。这并不是说这里面没有什么好东西,但总的来说,我现在说的每句话,我都已经(想象着它被发表了),就像那个刻薄的、脱离现实的家伙(引用)一样。我不生气!这很刺激,但不是我的菜。
你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我只是想让自己待在一个有挑战性的地方。前几天我读到一篇关于Lollapalooza的评论,上面写着:“NIN是另类摇滚时代唯一一支着眼于未来的乐队。”谢谢你!当你做了20多年的事情,你很难客观地看待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可能是他们父母最喜欢的乐队,诸如此类。如果我往外看,认为这只是一种怀旧行为,这里的每个人都和我同龄,挤在万圣节的服装里重温我们在大学时的美好时光,那就很清楚了。我需要好好照照镜子,然后说,是时候开始为电影评分了。或消失。
在我看来,我一直在寻求重新发明,而不是忽视我的目录。我想给人们一些他们认为可能会得到的东西,但同时也挑战他们,推动他们做下一件事。但随着口味和文化的转变,很难做出判断。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很酷的“独立”乐队,如果当时有独立乐队的话。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就会变成,嘿,你现在属于那个类别了。忏悔式的歌词超过了侵略性的音乐已经过时了——你应该留个胡子,演奏他妈的假民谣,不管(流行趋势)是什么。所以我只想活得比所有人都长,直到成为一个老男人成为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