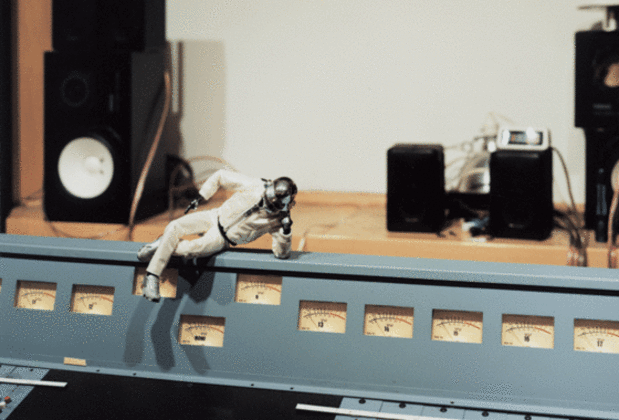阅读马修·施尼珀关于下一波纽约舞蹈厂牌的专题DFA记录跳后。
故事马修Schnipper
摄影安娜·鲍尔
乔纳森·加尔金好心地给了我一个百吉饼当他告诉我Syclops不接受采访时。加尔金是舞蹈厂牌DFA的合伙人,他与联合创始人詹姆斯·墨菲(James Murphy)和蒂姆·戈德斯沃西(Tim Goldsworthy)一起,指的是Mu的DJ兼制作人莫里斯·富尔顿(Maurice Fulton),后者一直以Syclops的名义录制即兴电子乐。加尔金甚至没有试图假装他可以说服富尔顿接受采访或拍照,他只是给了我一个坚忍的和排练的“不”。不被人胡说八道感觉很好,坐在一个70岁以下还喜欢百吉饼上放白鱼的人对面感觉很好。
在很多方面,DFA的办公室就是Galkin的办公室。墨菲的LCD音响系统带着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巡回演出,把他从DFA阳光明媚的西村办公室搬了出来。戈德斯沃西也很忙——他最近有了一个孩子(他的第二个孩子),他更专注于生产,而不是商业。戈德斯沃西说:“我很擅长在某种程度上徘徊,然后说‘我更喜欢紫色’,但Excel电子表格之类的东西不是我的风格。”加尔金是一种沉默的合伙人(还有贾斯汀·米勒,沉默合伙人的沉默合伙人),他带着这种尊重在奔跑。
DFA今年有20首12英寸的单曲准备发行(来自Invisible Conga People, Juan Maclean和Pylon等),还有来自Hockey Night, Shit Robot和Syclops的专辑。还有一个由加尔金掌舵的衍生厂牌Death From Abroad,专注于更晦涩、非美国的舞蹈音乐。这种猛烈的生产激增始于去年年底,大量12英寸的产品来自新的、主要总部位于纽约的组合,这些组合可以追溯到DFA早期弥合家用电子产品和后青少年后朋克之间差距的时代。然后随着《Black Dice》的离去,以及《LCD Soundsystem》和《Hot Chip》的发展,DFA成为了主流舞蹈摇滚的代名词,而奇怪的乐趣也逐渐消失了。现在它又回来了。在2008年,把希望和商业计划都放在大量黑胶舞曲单曲背后似乎有点危险,加尔金认为没有其他选择。他在谈到音乐行业时表示:“现在的世界有点像时代错误,东西正在消失。”“与此同时,我觉得我们正处于游戏的巅峰。这有点苦乐参半。”

30年前,当舞曲首次出现在美国时,它是一种邋遢得多的文化。没有主流观众,没有伊比沙岛,没有荧光棒,只有经典R&B、新技术和日益壮大的同性恋俱乐部场景的有机融合。在芝加哥、底特律和纽约,DFA的主要支柱是室内音乐、电子乐和迪斯科,但在那里,DFA仍然是地下音乐。DFA始于Rapture,这支乐队之前曾在一家硬核厂牌上发行过唱片,后来才发现Gang of Four的背拍和轻拍其实有点时髦。The Rapture加强了自己的节奏部分,专注于高帽舞,并获得了惊人的成功,新人充当了舞蹈音乐大使,向不熟悉的粉丝宣传。现在,DFA已经成立六年了,艺术家和粉丝们都有时间和工具来吸收更广泛的舞蹈历史。尽管Rapture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狂热,但DFA今天发布的曲目是经过仔细研究的;在卧室里为卧室制作,俱乐部扬声器和耳机的音乐不再相互排斥。
也许这是舞蹈音乐谱系的自然变化。迪斯科已经有将近35年的历史了,它的大部分社会历史都没有被DFA的年轻艺术家们直接吸收。虽然这并没有改变音乐的声音,但它确实改变了它被听到的方式,从而改变了它的创作方式。Goldsworthy谈到技术带来的新便利时说:“我不再被当作电脑巫师。”这种不断进化的简单性让更广泛的音乐家领域出现;有了更多的糠,也有了更好的小麦。而这样的品质善良一直是DFA的一部分,以下艺术家-黑色流星,圣灵!《继续前行》、《大力神》和《风流韵事》——代表了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新标签:热情的男人在工作,把吸引力变成了21世纪的科学。

黑色流星
在国防部的人知道加文·拉瑟姆的名字之前他们都叫他"巫师"他是他们的合成器修理工,在地下室一个改装过的壁橱里工作。他总是被电子无人机所吸引,“想要创造一种有机而有活力的声音,所以当我发现模拟合成器似乎是完美的工具时……我在家自学了基本知识,在水槽里烧电路板。”他自己制作的合成器——红色的木架、金属板、五金店的旋柄和潦草的记号笔标签——仍然倒立在DFA工作室的角落里。
现在在柏林,Russom一直在以Black Meteoric Star的名字录制他自己版本的酸屋。“我有更多的空间来倾听和思考事情,”Russom谈到他的新家时说,但他的新音乐——DFA计划在今年春天以12英寸系列的形式发布——却没有任何暗示。它残酷而幽闭,原始的汽车后备箱低音拨浪鼓,扁平的铃铛,玩具汽笛和脉冲激光在破碎的鼓机上,以每分钟十亿次的速度跳动。起初,它听起来像80年代中期美国中部强硬的酸——尤其是因为Russom将它混合到卡带里——但随着层次的展开,它变得更加激烈、复杂和隐约令人恐惧。
在创造这种电子饮料之前,Russom发布了火星的日子2005年,他与合作伙伴迪莉娅·冈萨雷斯(Delia Gonzalez)录制了一张专辑,这是一张巨大的、没有鼓的梦境,是他一生对童年嗡嗡声的实现。他说:“甚至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喜欢连续几个小时按住风琴上所有的小和弦键。”他在今天的流行音乐中听到了这种有质感的丰饶。说到布兰妮·斯皮尔斯的新歌,拉索姆说他喜欢“光滑的表面,以及在表面下能听到多少气泡”,这就像在谈论他自己的音乐一样。虽然《黑色流星》和火星的日子它们往往大相径庭,与其说它们是对立的,不如说是颠倒的幽灵伴侣,一个是另一个的复活版本。

圣灵!
我真没想到能和圣灵一起去DFA的地下室工作室!开始谈论罗库斯但在青少年时期,《圣灵》的尼克·米尔希瑟和亚历克斯·弗兰克尔!是嘻哈组合Automato的成员。米尔希瑟还记得早年的那些日子,“你听Wu-Tang和Pavement。(他说这话时与其说是亲昵,不如说是听天由命。)“对我们那群朋友来说,那只是流行音乐。”Automato在说唱音乐中采用了这种自由放任的方式,他们通过对西区(West End)和序曲(Prelude)的单曲进行采样,学习了迪斯科的基本元素。很快,他们发现自己被琶音合成音和天后的哀号所吸引。“我有点不对劲,”弗兰克尔在意识到自己喜欢SOS乐队的一首歌后说,他吓坏了,就好像发现自己得了青少年疱疹一样。当他发现这些歌曲“在1978年大受欢迎”,而且“他身边的每个人,尤其是所有的制作人,都知道所有这些歌曲”时,他觉得自己很傻。 Alleviated by peer pressure and now more secure in their desire to make sugary disco, they’re delivering it in pure form.
“坚持住”,第一个圣灵!这首单曲是一首跺脚、吹口哨的赞美诗,带有电子钢琴的咯咯声和弗兰克尔的纽约普通人歌词:我爱这座城市,但我讨厌我的工作.他听起来像迪斯科爱好者法瑞尔(Pharrell),不完美,可爱得无可救药。《Hold On》如此亲切,在去年11月被选为iTunes本周免费歌曲后,最终在20万台电脑上找到了播放方式。YouTube上甚至有一段视频,里面是几岁的孩子随着这首歌的加速版跳西班牙舞,这无疑是一首热门歌曲的标志。圣灵!的新曲目——分为12英寸和更民粹的LP-lean,与Chic的强大泡泡糖和Stevie Wonder的复杂快乐相呼应。Frankel解释道:“我倾向于被那些真正具有吸引力的内容所吸引。”他们也模仿了这种普遍性。的音乐是躲在一间小公寓里的两个人演奏的简单的放弃伪装的声音。

仍然
埃里克·邓肯看起来有点像帕特里克·斯威兹点休息.由他和丽芙·斯宾塞(Liv Spencer)组成的邋遢派对二人组《依旧在走》(Still Going)的基调就是他刻意的慵懒。他们既是朋友又是邻居,在斯宾塞威廉斯堡的工作室(他的日常工作是为广告配乐)合作,并于去年年底为DFA发布了首款12英寸的产品。“Still Going Theme”是这对组合的目的宣言——拍底的低音和“听起来真的很便宜”的键。斯宾塞说:“《Theme》并不是真正的一首歌。“我们的想法是把它简化为最简单的组成部分:什么会让人们想在舞池里工作?”他们决定采用简单的方法:钝边铜鼓的基本循环和向后的渔网的轻响。这首歌在六分钟后就结束了,但它蹩脚的钢琴伴奏可以无休止地循环(b面被命名为“On and On”可能不是巧合)。
邓肯也是纽约二人组rub -n- tug的dj之一,他知道如何从展台的商业方面发挥作用,他用不知疲倦的节奏调和Still Going的晕眩。邓肯说:“那些去夜总会的人,就是我们追求的人。”这使得他们的布吉创作品牌不同于其他专注于家庭的DFA艺术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努力仍然是一样的。随着今年晚些时候推出的12英寸新机型,他们将加入假声钩子来增加朗朗上口的因素,尽管这些声音仍然没有被录制下来。这些曲目的器乐小样有鲍勃·西格吉他独奏的傻傻的碎片和1981年迪斯科舞厅的康加舞曲。它们既有趣又简单——缺少装饰就缺少分心。“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斯宾塞说,“人们去俱乐部,忘记他们糟糕的一周,或者他们美好的一周,就像跳舞到太阳升起一样。”

赫拉克勒斯和爱情
安德鲁·巴特勒挂好我的外套后,兴奋地告诉我沃利·巴达鲁的事。Wally Badarou是时髦的新浪潮乐队Level 42的键盘手,Butler有他1983年的个人专辑回声从袖子里出来。我们在巴特勒的小公寓里,周围有十亿张唱片,门边有个水槽,沙发上有只猫。Badarou的合成器马戏团在立体声播放,巴特勒解释了他和DFA的蒂姆·戈德沃西是如何第一次在单人massive上建立联系的回声.Goldsworthy制作了Butler的同名专辑《Hercules and Love Affair》,并因为Butler的舞蹈背景而与他产生了直接的联系。但巴特勒并没有寻找一些无定形的、无法形容的“真实的”舞蹈声音,而是提出了跨越类型、感觉和风格的各种想法。“听菲利普·格拉斯的音乐就像听电子乐,”巴特勒说,这种关于跨类型扩展的基本和庆祝逻辑是《赫拉克勒斯》和《爱情事件》的关键基础。
继他的首支DFA单曲“Classique #2”之后,又推出了12英寸的“Blind”。真正巨大的,这首歌是巴特勒的史诗,层次的现代构成的脉动与安东尼赫加蒂的流畅的天后人声之上快速和诡谲的迪斯科。“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对经典的house非常兴奋,”巴特勒说,他发现自己在寻找这些歌曲采样的迪斯科歌曲。他说:“在我听过很多次采样的声音之后,听到原版的感觉就像在天堂一样。”“我的注意力从现代舞曲转向了古老音乐。”这种广泛的品味在他的专辑中很明显;“Easy”听起来像亚瑟·拉塞尔(Arthur Russell)在他的晚期浪漫中使用了软绵绵的技术,“You Belong”听起来时而像迷幻屋,时而像freestyle,带有流畅的人声口音,“Iris”就像欢快的三联舞,带有准备好了的铜管和阳光。“我创造纪录的目标是
我想要做好听的,完全好听的舞曲,”巴特勒说。“我不想只做跳舞用的音乐。”虽然这张专辑在美国的发行日期还没有确定(它于3月10日在欧洲发行),但巴特勒说,DFA将发行带有混音版的单曲和带有“更柔和歌曲”的原创b-sides。这些歌曲温柔而安静,与舞蹈音乐紧密相连,在它的大部头之间穿梭,却不一定要进入它。但是,就像巴特勒怀着浓厚的精神所做的一切一样,他们仍然是不可言喻的大力神。